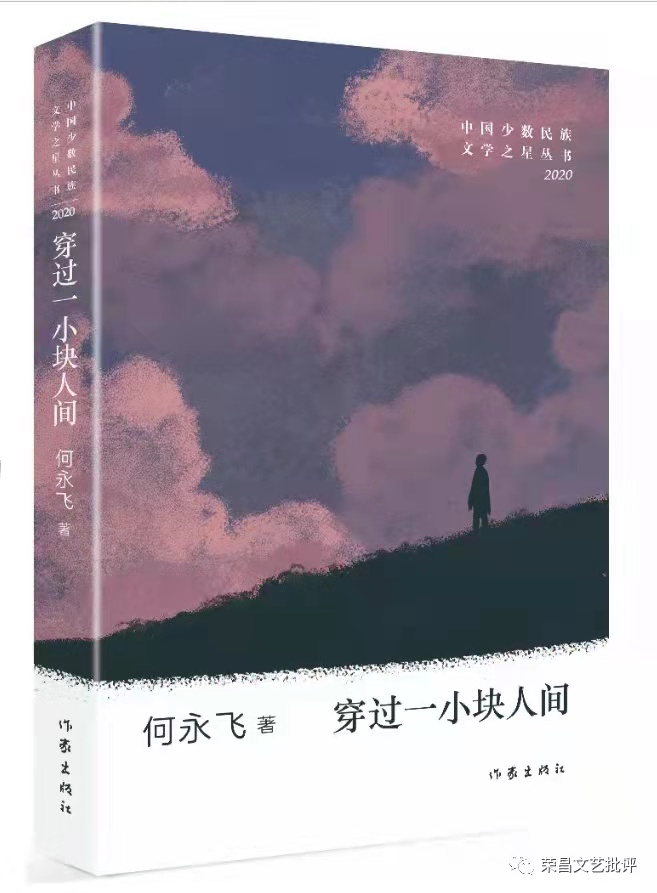
滇西高原是白族青年诗人何永飞的灵感策源地和重要的抒情场域。在二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中,他紧紧扎根于这块肥沃的文学土壤,书写出众多彰显自然人文风情和饱含民族心理情绪的优秀作品,形成独特的诗歌风格,获得了包括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在内的多个重要文学奖项。《穿过一小块人间》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之一,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分为四辑,分别以“大风歌”“地阔赋”“悲愿帖”和“心路图”来命名,可感知蕴含其中的地理特质及心路历程。
诗人对脚下的土地寄予了深切感情。站在山长水阔的大地上抒情,他的目光穿过岁月的帷幔,勾勒出这片土地的前世与今生。纵横云南高原的多条铁路如同一根根粗壮的血管,将边疆与中原连为一体,注入了强劲的生命活力。诗歌《云上之路》将历史传说与现实景象交织,写出云岭大地独特的气质,而当年修建滇缅公路的悲壮与艰辛,牵引出对抗日战争史的回溯,使诗歌有了更深的历史维度。《溜索,再见》则是对现实的观照,在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彩虹桥连通了独龙江两岸,昔日血泪浸染的溜索成为永久的记忆,幸福生活由此开启。在人类进步的征程上,也有过意外和挫折,但是一次次的劫后余生,一次次的灾后重建,靠的是人类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和创造力,《劫后的村庄》表达了对人们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由衷赞叹。
在何永飞笔下,村庄应是充满活力的,这是精神的原乡,亦是乡愁的来源。《乡村命脉》构筑了一幅生气勃勃的乡村画面,这里鸟鸣悦耳、牛羊成群,蛙声阵阵,垂钓者、耕耘者、安闲者,各行其乐,“放眼望去,草木和人群在拼命地往前冲”,乡村的“命脉”靠的就是这些充满动感的景象来维系。在村庄日益空心化的当下,这种对于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的追寻,不仅可以激发出无尽的乡愁,而且对于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乡村伦理,也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在诗人看来,尽管只是身处“一小块人间”,但从这里可以窥见世界的面貌,《村子大事记》以颇具代表性的情节回顾,将村庄的历史串联起来,在充满艺术张力的诗歌叙述中,某个具体的乡村事件具有了更为复杂而宏阔的历史象征意义,群山深处的村庄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变迁的缩影。诗人自信地站在故乡的地理坐标上,以自我经验观察世间万象,以诗歌写作实现与阔大的世界进行灵魂对话。在诗人看来,现实世界也并非全然晴天,也有阴翳,如过度的城镇化追求,往往以伤害村庄的本来面目为代价,《田野之今生》写出了盲目的城市扩张蚕食了原本诗情画意的田野,引发了一系列危机,使乡村前景堪忧,人类将自食其恶果。诗人对此满腔忧愤。
何永飞的诗歌之旅从滇西高原启程,这片土地赋予他灵感的同时,也铸就了难以磨灭的精神底色。这里自然山川秀美,文化多元并包,多民族和谐共生,精神信仰各有其特色。这种绚烂的精神气象是由众多生活于此的普通人日常的言语行为来彰显的。他们普遍尊崇万物有灵观念,神灵的行迹遍布每座山川每条河流,《仰望星空》表现了对亡魂的留恋,在人们意识中,亲人亡故之后是“去了天上”,变成了一颗颗数不清的星星。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还体现在对世间万物包括弱小者的珍视,《给一只蚂蚁下跪》表达了深切的悲悯情怀。但高原人对生命的尊敬不是无选择的,可以下跪蚂蚁,却不能下跪豺狼,这是值得敬佩的自然观和伦理观。
少数民族诗人似乎天生就对生态话题敏感,这与其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主要体现为呼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批判屠杀动物的野蛮行径和破坏家园的愚昧行为,充分证明了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学的写作伦理。对自然的敬畏感,对万物有灵的坚信,无意识地转化为一种与自然求和谐的审美理想。何永飞的诗歌中关于生态的篇幅较多。自然万物都有其运行的规律和法则,生态链是一个完整的自然体系,人类的凶残和贪婪,让其失去平衡,不仅物质方面的积累容易顷刻间毁于一旦,精神也将面临虚空,失去敬畏和信仰之后,变得迷茫而无所依凭。由于过度开发,自然生态极为脆弱,环境恶化,疾病随之而来。《虎王哀歌》书写的是生态遭到破坏之后的景象,诗歌以“虎王”被捉进动物园成为供人观赏的玩偶的遭遇为线索,呈现出人类对于昔日森林之王的无情伤害。诗歌以“虎王”之哀写人类之恶,发出了义愤填膺的呐喊。作为诗人,他承担着对这个世界作出判断的责任,那些违背自然规律,泯灭人性的现象在诗中均将遭到谴责。《惊闻》以一组看似悖论的现象,书写了这个世界存在的乱象。《记录,或警醒》则是反思疫情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诗人并非无节制地控诉,他也在寻找建设性的出路,《神临记》和《大地悲心》体现了向内心深处掘进的自觉,尤其面对诸多现实困境时,人类应该寻找和解的途径,寻求内心的宁静,达到更为稳定而和谐的境界。
诗歌是诗人形象的外化。在何永飞的作品中,体现了他作为高原行吟者的特征。他把奇崛的自然山水收入诗歌的行囊,变化出的却是一首首整饬之作。这些作品虽非全部押韵,但是抒情叙事均在相对规范的格局之中,没有太多的旁逸斜出,体现一种整齐之美。这要求诗人对诗歌意象的营构,对节奏的把握都恰到好处,语言在各自位置发挥象征意义,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诗人充满悲悯的心绪也在含蓄隽永的语言中展现无遗。
——本文发表于《中国民族报》2021年4月16日“文化周刊”。

